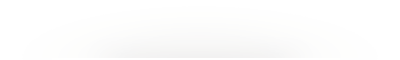
文/吳元海

寒假里,翻看《論語》,讀到《論語-侍坐章》中《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西華侍坐》。
文章生動再現了孔子和學生一起暢談理想社會的情形。
子路的輕率急躁,冉有的謙虛,公西華的委婉曲致,曾皙的高雅寧靜,給人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。這一段可讀性很強的文章,讓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關于掛歷的往事。
八十年代初期,父親退休后,被剛剛復立的人民保險公司聘去,做保險工作。
到年底公司總結的時候,父親帶回家四箱掛歷,用以贈送給客戶。 那時,十多歲的我,立即被印刷精美的掛歷所吸引,迫不及待地翻看起來。
掛歷冊頁上有電影明星,靚麗多彩,賞心悅目。有盆景,精巧別致的疊石和花草樹木組合在一起,巧奪天工,不禁贊嘆制作者的匠心獨具:一盆,攬天地之精華,一景,裁匠人詩意之意境。還有風光攝影,祖國大好河山在作者的鏡頭里,或大氣磅礴,或明媚委婉。
印象最深的是一幅月亮圖,從開始的上弦月、滿月、下弦月,一共十五個月亮,成弧形排列在朗朗夜空之上,小小年紀的我,張大了口,驚訝得說不出話來,太神奇了!太美了!
還有一本掛歷,是手繪的國畫,畫的是孔子和他的學生們,上面還有一些文字,我卻看不懂。
父親讓上高中的四哥解讀一下,四哥說是《侍坐圖》,講的是孔子的故事。四哥把文言文給翻譯出來,然后開始講解。
四哥不愧是高中生,面對父親,二哥,三哥和我,娓娓道來,特別是:“莫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風乎舞雩,詠而歸。” 夫子喟然嘆曰:“吾與點也。”翻譯出來就是(曾晳)說:"暮春時節(天氣和暖),春天的衣服已經穿著了。(我和)五六個成年人,六七個少年,到沂水里游泳,在舞雩臺上吹風,唱著歌回家。" 孔子長嘆一聲說:"我贊同曾晳的想法呀!"
父親和哥哥們一直贊同這個說法,議論紛紛,都有自己的見解。
可是,我怎么也不明白,為什么在春天到河里洗個澡就是理想的社會?我們不是經常這樣嗎?
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,直到上師范后,自己讀到了這篇《侍坐章》,才知道,曾皙是主張以禮治國,他說的是禮治的結果,是太平盛世的圖景。
一個自由,文明的社會,確實是每個人理想之治,幸福社會,看似很低的要求,實則是很高的精神追求。
我挑選了十幾本掛歷,央求父親不要送人,可是后來還是被父親送人了,只留下了那兩本“月亮”和“侍坐”。那本“月亮”的掛歷掛在我的房間,那本“侍坐”被父親掛在他那間。
參加工作后,我的第一份年貨就是一本掛歷,我很珍重地把掛歷拿回家,掛在我的房間里,生活和工作中的重要大事都一一記錄在上面,以便提醒我去做好每一件事。
掛歷由皇歷、日歷、年畫逐步演變而來,是歷書與年畫相結合的藝術品。
香港著名英商太古洋行第二任華人買辦莫藻泉上任后,1884年他推出一種類似海報廣告式的“月份牌”,用以宣傳太古糖廠的產品。
隨著歲月的流逝,“月份牌”逐漸演變成為當今的掛歷。如今更趨于電子化,所有的電子通信設備幾乎都有日歷本,其功能和掛歷如出一轍,可以記事,備注出行,查看黃道吉日等功能,可謂方便。但是,掛歷的精美,它帶給人們的審美享受和文化教育,永遠都不會消失。
掛歷記錄的是一年年時間輪回,記錄了每個年代人們獨特的生活。